为进一步巩固学风建设长效机制,激励学生通过寝室内部的自我管理与互助学习,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共同营造勤学善思、奋发进取的学习生活环境与“以寝风促学风、以学风促成才”的优良学风氛围,新葡京网上赌场
开展“一站式”学生公寓学风建设月活动。在“法学典籍漂流计划”主题活动中,新葡京网上赌场
青年教师参与法学典籍推荐,为同学们开拓法学思维、积累专业知识提供指引。
荐书人
何赛:法学博士,新葡京网上赌场-线上娱乐平台
国际法教研室专任教师。中国海商法协会成员;黑龙江省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黑龙江省法学会俄罗斯法制与法学研究会理事,黑龙江省专家技术领军人才民商法学梯队成员,东北亚法律查明中心外国法查明专家。
推荐理由:如果一个人一生只能读一本法学专业书籍——毕竟人生有更多重要的事情应该去做,那么拉伦茨与卡纳里斯的《法学方法论》将会是不二之选。本书在德国多年来一直是法律方法论方面的经典教科书。除了掌握个别法律部门的知识和解决案件的实践运用外,掌握方法论工具对于成功学习也尤为重要。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解释理论,该理论通过德国最高法院判例法中的大量实例加以说明。克劳斯-威廉-卡纳里斯继承并更新了他的老师卡尔·拉伦茨的精神,同时也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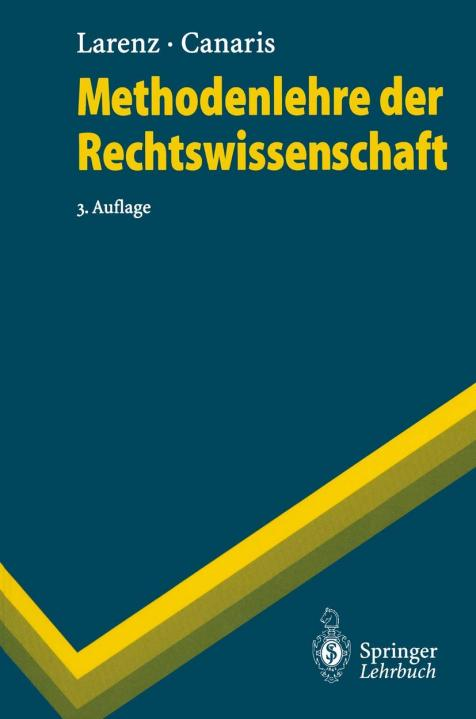
拉伦茨的著作在亚洲掀起了一阵狂潮,直到今天仍留有余韵。近来市面上被冠之“法学方法论”的书籍汗牛充栋。例如:克莱默《法律方法论》(杨万里译)、默勒斯《法学方法论》(杜志浩译)等等。那么缘何我仍要推荐这本首版于1960年的著作呢?易言之,拉氏《法学方法论》有何独到之处与不可替代性,时至今日仍使广大师生心向往之?
一言以蔽之,拉氏著作最富魅力之处在于:娴熟地运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构建起了精致的私法方法论大厦。
我曾在哲学讲座中听闻某位学者指出,据称中国人最喜欢的西方哲学是黑格尔哲学,而非时下流行的英美分析哲学。其实,在吾人的性格中始终对“终极问题”有着强烈兴趣。远者如太史公言:“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者如吾黑大之校训:“博学慎思,参天尽物”。吾人对老庄之学《道德经》《南华经》的解读亦从未止息。质言之,拉氏著作之所以风靡吾国,系其内里之思辨精神与吾人究天问际之品格偶相契合,而非他者。
近年来,对拉氏著作之批判时有发生,后文就“本书之争议”“译本之选择”“阅读路线推荐”三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本书之争议
拉伦茨在第三帝国时期被封为“桂冠法学家”,因其与NZ之间过从甚密的关系而被认为存在“历史污点”。这里不打算对其生平进行介绍,学生可以通过黄瑞明《NZ时期的拉伦茨:德国法学界的一页黑暗史》文章具体了解其思想与故事。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张志伟教授在谈及海德格尔时——该君亦与NZ有关,举了一些例子:康德曾为获得教授职称转向俄国女王申请;卢梭从未遵循基本道德标准;尼采身患梅毒;维特根斯坦与福柯是同性恋者;罗素在80多岁时还在猎艳;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婚外恋等等。
我以为,评价学者应抱持“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对其个人言行应当用道德伦理来评价;对待其观点应当用学术标准来衡量,当然二者并非迥然轩轾。中国亦有“立德”“立言”“立功”的三重评价标准。固然于此等价值三元上,德行占据支配地位无可辩驳,但彼等之牵连与影响,亦应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当存在于脑海之中的思想转化为铅字后,它就成为了一种独立于主体与时空的永恒存在。质言之:它就成为了一种可资独立评价的对象客体。拉氏曾为权柄与名望而理论化NZ之纲领,在战后几度文饰其在第三帝国时期的作为,不仅毫无悔过之意,反而纵容其门生攻讦对其进行批判的吕特斯和雅可布斯等人。这固然令人愤慨,但仍应保持理性考察其作品是否仍残留着有害思想。
其一,拉氏始获国际影响力之著作均为1945年后出版。其二,拉氏作为“新黑格尔学派”的主要成员,虽然在第三帝国时期屡次通过简化甚至曲解黑格尔哲学来证成国社主义,但实际上黑格尔哲学本身与国社主义并无任何亲缘。其三,在《法学方法论》中,拉氏仍然援用黑格尔哲学中的“具体而一般之概念”及相同思考方式的“类型与类型系列”,这会导致吕特斯所谓“无限制之解释”。因而,吕氏讥嘲拉氏《法学方法论》系“方法论上的盲目飞行指南”。但这正好在侧面说明了,该书已将错误之思想涤除殆尽。我以为,对方法论不能抱有任何价值上的期待。毕竟,出鞘利刃既能砍瓜切菜,亦能行凶伤人,紧要处系主刀人的价值判断。
就该书之地位与影响的获致,有人认为是拉氏籍其弟子卡纳里斯之名,非出自拉氏本人。我以为言过其实。尽管卡式名声斐然,但不及拉氏之争议性。后者无论是在战前与战后,美名与恶名皆具于其身。出于批判也好,出于赞美也罢,其著述系当时德国法学界热衷研究的对象。再者,拉氏在去世前两年仍在进行关于此书的修订工作。如果说本书取得的成就与其无甚关系,亦属不客观。此外,在德古意特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学生报告中的20世纪德语民法教师》中明确指出,卡氏系“继承”了拉氏法律思想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关于译本的选择
目前拉氏著作分有台北大学陈爱娥教授与西南政法大学黄家镇教授二译本。陈译本之优点在于文风古典优雅,赏心悦目;缺点亦犹晦涩然。这是陈译的一贯风格,譬如陈译的二卷本《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为观察重点》。再者陈译本之底本为“学生节略本”,不包含“历史批判部分”。这极大地影响了读者对拉氏观点的理解。而黄译本除在翻译上补全了陈译本所缺失的内容,其在用词上更加符合今日之惯习。虽有人批评其对书中提及的日本学者名讳有翻译错误之虞,但此等瑕疵实乃无伤大雅。
以我之浅见,陈译本兹有如下问题。第一,翻译不规范。如将Regelung译为“规整”,让人不明就里。似应译为“规定”。盖因译者认为该词派生于regeln,但实际上应取Vorschrift之意涵。Regelungszwecke被陈氏译为“规整的目的”,黄氏译为“规范意旨”。又如,将Konstruktion译为“构想”,实为“(体系的)构建”;将Qualifikation译为“品评”,实为“定性”。根据拉氏后文所给出的例子,即对先买权属于形成权抑或附双重条件的买卖契约的论辩可资为鉴。第二,不明意义的增译。陈氏频繁使用“该当”一词。初读以为与康德所用“应然”(Sollen)同义,实则德文原版根本查无此词。究竟如何理解“该当案件”(p5)“该当情况”(p193)?第三,翻译错误。将Teilsystem译为“(部分)系统”(p320),实为“子系统”。此系望文生义。该词处于拉氏体系建构方法之核心地带,若词不达意,则通篇不知所云。
关于阅读路线之选择
传统阅读路线:杨仁寿《法学方法论》——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齐佩利乌斯《法学方法论》——拉、卡《法学方法论》(黄家镇全译本)。
传统阅读路线之弊端在于,切断了法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在黄书向齐书的过渡中,会遭遇不可抵抗之挫折。实际上,拉氏著作的璀璨夺目之处正是在于其所浸淫的深厚哲学思想,如若抛弃之,则完全失掉其阅读意义,那和阅读仅被称之为“法学方法论”的一般著作没有任何区别。
我推荐的阅读路线:邓晓芒《德国古典哲学讲演录》——康德《政治哲学文集》(李秋零译)“法权论的形而上学初始根据”章节——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张译本)——拉、卡《法学方法论》(黄家镇全译本)。
此路线将拉氏法学之哲学前提,即康德与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以较为顺畅便捷的方式予以勾勒,为学生透彻理解拉氏之思想奠定了基底。非经此路线,拉氏著作不可甚解。